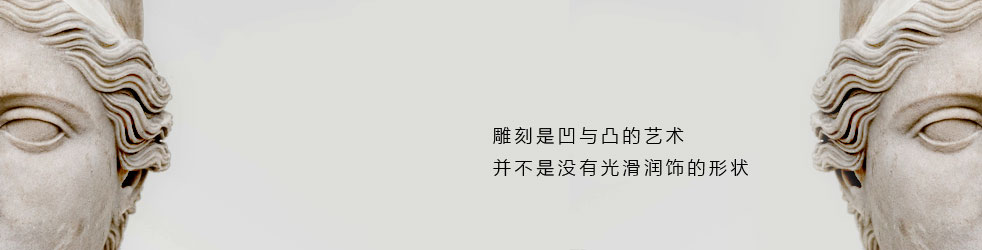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我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人,自我15岁开始艺术学习的时候,我就笃信自己对周边环境的感受,而且凭借这些感受来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构思自己的艺术作品。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注重自己的感受,相信这种感受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一切。
我不敢称自已是个中庸的人,但我一直欣赏这种生活态度,并试图把中庸作为自己生活的信条。虽然在感性的驱使下我经常做一些事后让我后悔的事,但我仍然特别敬仰那些非常中庸的人,虽然今天我身边的诱惑不断、冲突不断,但我还是刻意地驱赶不时传送来的诱惑、平熄内心的冲突,尽力去恪守中庸之道。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无论出了什么事我的内心总会拷问自己,我会战战兢兢地追悔我做的事对他人造成的的影响和侵害。我会刻意的去逃避会使我承担责任的事,我不时依懒一个清冷的感情角落来抚平内心无名的惊慌。直到今天,一个冲突四起的时代使我更担惊受怕的躲在那个清冷的角落。
我是一个较真的人,可能是遗传的原因。我不是能轻易梳理开内心矛盾的人,更不会轻易放弃那些矛盾。我计较与我有关的一切,我会在内心计较所有的人。当我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候这种计较也会激怒我的情感,在情感的燃烧中化做一团薄雾而暂时漂离开,但直到今天我仍计较着那些我内心至今仍然没有答案的事情。
我走过的:“路” 我出生在1962年,中国的“文革”后期我开始读小学,我在幼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是一种理想式的共产主义教育。我记得我们上学的第一天就在书包中端端正正地放进一本“宝书”,这本书就是《毛主席语录》。此后10年我们这代人就在这本“语录”的指导下成长起来了。如实讲这部中国人当时的“圣经”教育了我们,在我们去实现伟大理想的实践中,我相信每一位有幸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过非常狂热的真诚信仰,始终不逾直到今日。当我带上红小兵臂章的那一刻,当我带上红卫兵臂箍的那一刻,当我举手面向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宣誓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都能感受到那份激动和真诚所带来的自豪和骄傲。我们真诚的信仰过,那份真诚可能夹杂着无知,可是那份真诚、那份特别的真诚在10年后我再也没有深切的感受过。今天想来我能津津乐道地回忆那个时代,我想我的血脉中流淌的血确定无疑沾染上了那个时代的“红色”,享受过当年的那份真诚,并且一直铭记在心。
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人家,父母都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出身于“地主”和“上中农”的家庭,应该受教育的年代他们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的。当他们思想成熟时却赶上了一个非常朴素和非常正直的时代。他们可能享受到了比我更多的激动。因此,我想我个人性格中的部分特征是受到他们自然和良好的遗传,当然也包含了价值观的确立。中庸、胆小、计较可能来自于他们的身教和言传。我爱我的父母这是人的自然属性,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关爱孩子的家庭,所以我也不自觉地投入到他们的怀抱。我一直为我能使他们感到满意而骄傲。我的父母非常注意用他们的言行影响自己的子女,把他们的价值理念、生活准则、审美态度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因此朴素、真诚、循规蹈矩、胆小中庸,便成为我们家人自然的性格标准。
我从小喜爱动手劳作,对有形的东西比较偏爱,幼时画过一些街道上的东西经常被人夸奖。以后自然乐于写写画画,小学、中学时期画黑板报、刻蜡纸小报、画宣传画,常常乐此不疲。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因绘画特长被老师推荐考入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开始了正规的艺术学习。
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是我接受正规艺术训练的开始,我在这所学校接受了比较全面的基础美术教育。“文革”刚刚结束,艺术教育在停顿了若干年后才得以恢复,美校的教师从不同的角落被召回,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各有所长。再有当年刚刚恢复招生,教学重点、培养方向、课程设置等等还没来得及细细研究,混乱之中我们就开始了学习,因此在四年的学习中我们掌握了中外古今各种艺术造型方法。中国书画、篆刻、素描、白描、西洋的水粉画、图案设计、雕刻、造型设计、陶瓷、玉雕等课程五花八门,老师各显神通,我们在多样的技术训练下掌握了造形表现的基本方法。
美校四年的技术训练,启发了我对雕塑的热爱,同时也培养了我对空间、形体的敏感。我的老师也发现了我对立体造型的特殊兴趣和敏锐,她的不断鼓励使我加深了对雕塑艺术的了解,并且形成了我的专业追求。当然这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兴趣,那时对技术的爱好是第一位的,对艺术的理解也非常的粗浅,大多停留在表现层面上。
1984年在不断升温的对雕塑的兴趣驱使下,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开始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出于对雕塑艺术的热爱,当时我怀着对我所认识的大师的崇敬立下苦志:努力把自己化做一块可以吸入无限营养的海绵,使出全力去学习。怀着这种这种毫无艺术创造和变革的心态,我开始了5年的专业学习。我一直试图做一名好学生,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学生。我在平日的学习中努力去领会教授们的每一个专业要求,总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的位置,总在内心怀疑自已的理解和表现能力,一切按教授们的要求去做。我时刻去感悟教授们传授的知识,力图使自己的艺术功底尽善尽美。
现在想来,我确实把教授们的古典主义技术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整的吸收过来了。这可以在我的本科毕业创作作品中看出来。大学期间我当之无愧是教授眼中的好学生,我的专业成绩一直较高,为人处事也得到了好评。毕业时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留校任教了,当时可能是以一个比较优秀的专业继承人身份和形象留校任教的。留校任教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诱惑,我幼时所形成的价值标准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我的艺术事业所需的创造性、反判性、革命性,由于自身的原因并没有得到任何自我的、他人的开发。那种朴素的、驯服的、善意的性格被鼓励和回报。一切都是那样的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内心还有些沾沾自喜,只因为我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这一时期我所确立的目标是打下一个优秀的专业技术基础,埋头于对写实泥塑技术的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量的、反复的习作练习并没有使我厌烦,所以我没有心思对社会上的文化动态进行关注。这一时期是我最不关心社会文化发展动态的一个时期,以至于八五新潮美术的时髦与思考都引不起我的兴趣。
九十年代初留校任教的内心甜蜜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我在教授的鼓励下创作了一件《鲁迅像》。这件《鲁迅像》是我艺术创作生涯中最自喜的极点,也是我艺术创作生涯中最自卑的极点。谈到自喜,我所生活的时代、我所身处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深信我是为了大家的快乐,为了前辈们已经钦定了的目标而奉献上自己的所为。他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所作所为就是给我所依赖的人们带来快乐。《鲁迅像》从构思到制作一直受到教授们的鼓励。直到我把这件作品送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展,我还一直在长辈们的恳定语态中享受着快乐,我对我所掌握的写实主义的基本技术和创作方法而自豪。
谈到自卑,1992年原浙江美术学院的同行向我发出参加《中国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的邀请函,这时我才隐隐约约感到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我有些不着边际的搜寻我身边的一切,有些茫然。我实验性地做了一些稿子:一些蒙着双眼行走的人。但这个尝试没有使自己满意,因为我正在感到茫然,我不知自己走向何方。我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茫然”的意义,所以我并没有把《蒙着双眼行走的人》做完。最终我还是把我做的《鲁迅像》送到了杭州。杭州在我的印象里是个最美丽的地方,1992年她带给我的却是痛苦的回忆。当我把《鲁迅像》陈列在展厅时我才发现我作品周围的东西是那么耀眼,它们并没有什么新奇,只是我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自己读起来都显得那么陌生。造型技术在这里显得那么苍白,《鲁迅像》失去了血色。这时我才感到我同时代的距离,同同行的距离,同艺术的距离。回头看我自己走过的路,就像是每一步都看着自己的脚一样,注重的是姿态、位置……我从来没有抬起头来看过远方,从来没有转转身子看周围,我忘却了自己要走向何方。
我正在走的“路” 从杭州回到北京,我开始寻找我要走的路,我开始寻找我能看到的一切,我在内心不断追问着自己:我到底迷失了什么?
我知道我的感情上的好恶,我知道这些年我丢掉的正是我的感情,而我的感情正是我为什么要学习艺术的初衷。回视我做过的作品,回视我情感曾经有过的关怀,我才意识到我做毕业创作时曾经有过的一丝快慰。1989年我的毕业创作是《戊戌六君子》,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六君子是清朝末年维新变法的牺牲者,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为中国自强而牺牲的知识分子。当时毕业创作时的主题就是想借用这个历史题材来转述我对现时推动中国改革的志士仁人的关怀。主题的选择是出自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因而也就非常快的得到了教授的认可。后来在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反复做了大量的构图稿,对雕塑的技术语言进行了不断的实践,慢慢又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技术状态,因而也就淡忘了作品创作时的原发意图。我把艺术创作最重要的那种现实关怀丢掉了。现在想来我应该把丢掉的东西拾起来,我应该对我的民族、对我生活的时代、对我个人的情感负起艺术的责任来。
1993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慢慢地找到感觉,这种感觉来源于我对自己的反思,来源于对社会人群整体思想和生存状态的思考。1989年前后是个动荡的时代,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冲突不断,这种冲突加剧了我内心的紧张。虽然在1992年以前我没有刻意用艺术的方式来思考这种“紧张”,但到了我清醒的时候,到了我用艺术的眼光回视的时候,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强烈和清晰,像被重击之后醒来的回忆久久挥之不去。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抖动,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刺激之后的无法控制的抖动,是一种控制不住的抽搐。这时我想把这种可怕的感觉丢掉,可是它就像鬼魂附体一样使我深陷其中。我无法左右自己,像是进入了一种亢奋的感情状态,一种必须表达和发泄的状态。
于是1993年我开始动手创作我的《躯体系列》,我想把控制自己“躯体”的紧张和冲突表达出来,同时又想让我内心的抖动平和下来,以使那种紧张和冲突所承载的雕塑形体能够突显。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胆小的缺点暴露在冲突与较量的对比中,那种怯懦的抽搐是深藏在内心的,是我感受冲突和紧张的兴奋剂,是我用来对比观者的情感尺度。我想让人们看到的是力量的冲突,是我用朴素的钢钉打入“躯体”后的内力与外力的冲突;是我用绳索束缚那些柔弱“躯体”的束与脱的僵持和对峙。
在这次创作激情的爆发过程中,我在连续5个月的情感冲动中一下子完成了15件《躯体系列》的作品,直到筋疲力尽时我才罢手。本来计划把这批作品集中起来做一个个展,但这个时期我个人人生中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可爱的妻子腹中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和妻子相爱十几年的成果,当我望着妻子正在隆起的肚子;当我细细品味她渐渐变化的步态;当她依偎着我在晚春学院操场的那棵大槐树下踏着满地槐花散步时,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爱”,一种深沉而平淡的“爱”。在这种“爱”的不断积累中,我内心的那种“紧张”、“冲突”、“怯懦”和“抽搐”渐渐得到了安慰,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对我的安慰。这使我朦胧的意识到我内心是多么缺少爱,也正是我们的内心缺少爱才会使我们的内心充满着怯懦和冲突。我凝视着我的《躯体系列》,我不断地拷问自己:你们为什么表现得那么狰狞?你们为什么显得那么躁动……
我没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我只是停住了手,取消了展览计划,遏制了内心的躁动。因为这时我正在准备接纳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是我现实的孩子;还应该是一种我还无法界定的精神与情感的新生。
1994年开始,中国雕塑界真正在思考的艺术人活跃起来了,这帮朋友们非常的投入,大量的作品投放社会引起了反响。我处在那么一种特殊的“失语”状态下,我只能静下来默默地关注他们并且为他们喝彩。当时我还在思考,我还没有看清自己的方向,我的内心还充满着矛盾。其实自1989年以后瞄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年轻艺术家大有人在,利用这个社会现实逐步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影响传达给了中国的艺术界。由于我个人还算是关心这种影响的人,所以我在读这些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时,我非常注意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情感取向。令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了太多的狰狞、躁动、冲突和抽搐。这使我不安,使我内心的矛盾更加难以化解,使我更加难以自拔。那个我期待的情感与精神的新生更加朦胧。
我陷入了长期的痛苦中,1997年由隋建国先生推荐,我的作品《死的永生》被日本岩手国际石刻研讨会选中,因此我有机会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在日本期间我接触了许多雕塑家,我细心观察和研读他们的作品。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时间比我们长,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更加靠近西方,本来我期待能在那里看到一些更加刺激和前卫的东西,但令我失望的是我没能验证我的期待,起码没有看到刺激的东西。只是在我的朋友家听到一些正在日本生活的中国艺术家比日本人玩得还热闹的艺术趣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乐于在国外玩,而且玩的主题都是关于中国人的。
我有些迷惑,对世界当代艺术,日本人所掌握的技术、了解的信息及开放的程度都比我们多,比我们大,而我所接触的日本艺术家对当代艺术都那么平和,都那么一丝不苟。即使是日本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也比我们的同胞来的温和来的深沉。是大和民族不够开放吗?是日本人缺少足够的勇气吗?是他们失去了智慧吗?我想不是。这是因为从整体上,日本社会对新文化的接受,对实验性艺术的接受,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对假“开放”、假“勇气”、假“智慧”不屑一顾,因此那些浅薄的、生猛的、极端的、刺激的东西被艺术家视为一种畸途,没人以此来兴奋社会,兴奋自己,更没人以此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艺术家,是哲人,是救世主。
几十年来,我们的艺术家在社会分工中逐步独立出来,从卑浅的匠人一步升格为高尚的贵族。他们内心承载了比任何社会成员都怪异的社会责任。社会身份的变化要求艺术家不仅在物质上要具备贵族的气息,同时在精神上也要时刻警惕丧失高贵。也正是如此,物质层面上追求新技术和引入新的样式,“高、大、全、红、光、亮”盛行一时;精神层面上肩负起“唤醒民众,创新革命”、“警世”、“羁俗”的责任,用艺术来改造社会、影响民众。这种社会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创作心态的变化影响了每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精神上被贵族化,导致了原本的根基的飘浮,总是以一种俯视的角度,以一种至上而下的关怀来面对社会现实,反映社会,因而使艺术创作从根上开始脱离现实生活,脱离开真正的人,脱离开自我。因为即使你是真诚的,也始终端着架子;即使你从不想负责任也要看得高远;即使你很世俗做事也要赋予巨大的意义。艺术被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左右了,倍受推崇的“贵族”实际是左右我们头脑的社会潮流。就如同今日社会中流行的“傍大款”一样,我们的艺术总是期待着别人的欢颜,应该说这是我们艺术的悲哀。
陈丹青在《美术研究》1998年第一期上的一段文字说到:“我们过去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策,形成一种人格,就是眼睛看着画,心里想着领导的态度,当前的政策。今天呢,是手下画着,做着,心里想着谁来买,谁来选,行情如何,潮流又是如何。这也难怪。其实,当代中国自己的大文化也难自给自足,要靠西方的认同、点头,不是样样都要同‘世界’接轨吗?”
这是我们身负“责任”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们对真正艺术的迷茫,所以我们的艺术,中国的艺术才表现得沉痛、空洞和扭曲。这也正是我“紧张”“抽搐”的病因。
当我不再叫嚣,不再强烈抽搐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爱的存在。平和更能享受到爱,而叫嚣只能获得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心情下,1998年我开始了《小角色系列》作品的创作。当我平和下来,手中摆弄一小块泥土时,我感受到了我同它的亲和。这些泥土从泥块到泥片的反复摆弄,使我越来越感到我同泥土(后来是蜡片)间没有了距离。我做的作品尺寸非常小,小到你不能一眼看到它的光泽;小到你的目光需要前移来完成对它的阅读。它们是一群有形的生命:“我想到活在世间的那些小人物,象一片干枯的叶子卷缩在角落里迎接着永恒的云雨,闪烁着零星的光彩。我想遗忘它的生命,它却纠缠着我的灵魂。”我绝无夸张地看到了生命的弱小,看到生命闪烁的光彩。我不想放大它们,因为只希望人们认识它们的弱小和平凡。
我到现在也解释不了《小角色系列》作品本身,因为我没有站在一个什么高度上去把握它们,去概括它们,去表现它们,我只想着一种平和,我对抗着我感情中突暴的一面,我消解了我内心的不安和焦躁。我从创作中已经大大的享受到了平和的快慰,我活得越来越轻松和快乐了。虽然作品还加杂着一些苦涩,但这是我感悟到的真实。
1998年做完《小角色系列》展后,我被学院推荐获得了西班牙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大学美术系研修一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亲自到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亲眼去看一看,这对我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一个目的想观察一下欧洲人的艺术,看看大师的原作和艺术的发展动态;一个目的想考察一下欧洲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及西班牙文化特色。
西班牙同我国一样是个有着帝国背景的国家,十六、十七世界他们曾称雄于世界,后来虽破败了,但在西班牙人的现实生活中仍可以看到帝国时代的影子。西班牙民族闲散、大度,骨子里充满了自信和不服,性情激荡,富于火一样的热情。这个国度里曾出现过象委拉贵支、哥雅、毕加索、米罗、达利、高迪等艺术大师。虽然这个国家处于欧洲的边缘,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欧洲文明兴起以后,这个国家一直没有脱离开欧洲文明的光环。直到现在,虽然当代艺术流行于德国、美国,但这个国家的当代艺术也不能算是绝对的二流,他们有塔皮埃斯、洛佩斯、奇依达等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艺术浸透在西班牙人的生活之中,在艺术学校中,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学生有几千人,他们不是进校时就想当大师,更不是想当大师才进入学校,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喜爱艺术,把艺术当作生活中的一个部分,真诚的品味艺术世界的那份情致,把艺术当作生活中的一份美食。这美食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每个人各有偏爱。每一位艺术家都仔细、勤奋地体味他们所喜爱的味道,并不争执“酸”是第一,“甜”是第二,“苦”是第三……的地位与优劣。因此他们的艺术形态与趣味是多样的,而且始终如此。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艺术在西班牙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更广泛的服务于社会,让每一位社会分子都能从艺术中得到本能的满足,这才是欧洲艺术相对发达的原因。
欧洲是一个充分发达的欧洲,这里产生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产生了文艺复兴,蒸气机又推动欧洲人创造了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的现代工业文明。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平衡发展,使得今日的欧洲人在一般的政治诉求、经济保障、文化多样性方面都够得到良好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的基础源于欧洲相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保障概念,这是人文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
这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文明从本质意义上讲是建立在专制和集权条件下的封建文明。我们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这种专制和集权制度同欧洲的封建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的专制色彩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上的,它辉煌灿烂、博大精深。欧洲的封建制度少有专制和集权的色彩,部落、诸候非常独立,王宫、城堡林立,虽然战争不断,但这种封建文明里已经包含了不少自由主义的色彩。这种自由主义色彩导致他们最早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在封建文明的基础上,在垄断与反垄断、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中推动了自由民主概念的完善。
在他们的当代艺术作品中,以纯粹政治概念表示诉求的东西并不多,大多还是在独立的个体经验基础上表现出非常纯粹的文化关怀,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因素,但不是激烈的,不是我们的那种革命性。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反观我们的文化,自150年前被动的开放门户以后,大批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要求革命,要求迅速实现国家富强。“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彻底否定了旧的文化,提出了西方色彩浓厚的“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并且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聚集了远胜于旧秩序的力量,采用包括暴力手段来拯救中国,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之后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和手段再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旨在使中国进步的伟大实践,直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
150年来,在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的革命无比壮烈,冲突无比残酷,变革无比迅速。这使我们认清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的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专政的暴君;所以要发动和集中一个比暴君更强大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是无法打倒老暴君的。可是一旦暴君被打倒,在生死的革命中所形成的权威和这种权威所聚集的力量又成为任何人都不能控制的东西,它又成为了新的专制的暴君,它又在摧生新的革命。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革命产生暴君、暴君摧生革命的逻辑,培养了我们的革命习惯和思维的极端性。自由和民主成为行动的口号,而行使的方式又是反自由和民主的。我们的艺术也因而始终伴随着革命,伴随着政治。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这种艺术在红火的的政治色彩映照下被强势文化识别和认可,因为这是可考证的实证主义标志。
在欧洲我更加清楚的看到了强势文化的选择权力,他们把政治的自由和民主留给了自己,却用自由和民主来刺激中国的艺术。在这种整体的国际文化环境中,被推到角落又被提到中心的自由属于强势的西方。如果我们依从于西方强势给予我们的利益,刻意涂抹自己艺术的政治色彩或政治精神,并且用“走向世界”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成功的话,那么中国以及中国的艺术将走向纯粹的政治,从而也就彻底的失去了艺术本身。政治的确影响着艺术,但艺术不是政治。
走出了欧洲,使我认清了我们的基本问题:自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一切被推崇的革命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无疑是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国富强与觉醒进行的自觉的社会变革实践,我们一直在找寻最优的富国强民的办法。平均20年的一次巨大社会变革,使社会整体结构都要经过一次震动和变化。这样的变革速度使我们来不及深入的消化掉新生命的营养,这个生命就在另一个生命的降临中变得腐臭了。并且培养了我们不断调换味口的机能,最终使人们坠入革命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得了机械性的狂食症。没有了社会变革有人就没法活,艺术家就没有了艺术创作的灵感。即使到了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着花花绿绿的洋伞,挡住阳光,怕晒到那张政治的脸。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政治,内心想的也是政治。因而艺术也就无休止的伴随着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庸。
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往我们学的是术,是办法,是结构,是模式,我们没有学心,没有学那个真的自由民主之心。当下的中国艺术家也是多从西方的艺术模式中寻一些东西来丰富自己。观念了、行为了、多媒体了等等办法和模式,内心还是中国人的,即那种革命的心态。
我以为我们真应该学的是自由和民主之本质。学会不躁动,不赶流行,生活得象一个真正的人。这样中国的艺术才能从表象走向内心,才能表现出中国人的世界性。
我回国到现在,我一直试图将我个人的心态调整好。虽然我还在无时无刻地计较着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我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人,接受的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但我有意识的将自己逼入平和、中庸的状态中。
2000年我做了大量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还属于架上的独立性的作品,但我想说的东西已经同1998年的“亲和”、“国情”有了本质的区别。当我观看建筑物上的窗户时,当我看到地面上的沟眼时,当我凝视人们的目光时,我都能够体会出那份平静。这使我感受到了躁动的消失。我发现我可以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那种空间收缩的感觉是非常自我的,封闭的,因此也越发能把这批作品表面上附着的躁动加以静化。一切都集中在孔洞之间。好像时间在凝固。平和得可以让人忘记呼吸。我想使我的作品表面上的躁动淡化,使之退出对作品外形的把握,让人从目光的移动中得到心理上的沉静。这些是我对我个人,可能也是对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一种理想性的表现。
我企盼人的平和,企盼人能深入到一个人应该深入的细节,而不是只有表面的张扬。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应该做的,特别应该抛弃躁动而走向安宁,从激烈走向平静。我曾把自己看做一只小蚂蚁,我知道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应该冲出我的洞,去迎接和享受这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痛苦。我勇敢地告诉自己,只有冲出去你才能汇入激烈的洪流,洪流里才能有你的气味和影子。这气味和影子的相融相合所产生出的使蚁群变得伟大的激素,绝对让小蚂蚁体现出存在的意义。这种放大了的生命意义会使异类感到敬畏,使同类引为自豪。
我现在仍把自己看做一只蚂蚁,我是个弱者,我惧怕那洪流,但我已经看清那暴风雨是假的,它只是在天空中一阵惊过的阴云和雷鸣,我勇敢地发掘着我的洞。我并不惧怕自身生命的脆弱,不惧怕我赶不上逃亡式的拼争。其实我太需要静下心来营建我们的精神家园,静下心来安然地冷静地面对这个世界,轻松地去抚摸这场暴风骤雨,让它们安宁下来。天空终还是天空。
我欲使自己安静下来,虽然我内心的感情是激烈的。我想远离利益的驱使,我想企望大家同我一样追求平静、享受安宁。这就是我正在走的“路”,一条平静、祥和的路,一头连接着理性,一头连接着生命。
发表评论
请登录